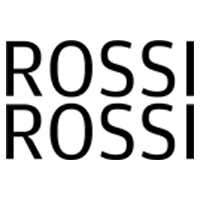紐約:林飛龍
By Emily Chun

WIFREDO LAM, The Casting of the Spell, 1947, oil on burlap, 109.5 × 91.4 cm. Copyright the Artists Rights Society, New York/ADAGP, Paris. Photo by Peter Clough. Courtesy Pace Gallery, New York/London/Hong Kong/Seoul/Palo Alto/Geneva/East Hampton/Palm Beach.
林飛龍:「想像力作用」
佩斯畫廊,紐約
林飛龍(Wifredo Lam,1902–1982)出生於父親是華裔、母親是剛果裔西班牙人的家庭。他創造了完全不可同化的繪畫,將歐洲的超現實主義和立體主義技法與他成長過程中的非裔古巴民俗儀式結合起來。大多數關於林的作品的展覽和研究都集中於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作品,即他在二戰爆發時返回古巴的時期。因此,這次紐約佩斯畫廊(Pace Gallery)與加里-納德藝術中心(Gary Nader Art Centre)合作舉辦的展覽,選擇以更易接受的時間順序探究他從3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作品。
1938年移居巴黎後,林先後結識了Fernand Léger、Henri Matisse、Pablo Picasso等著名藝術家。當中Picasso尤其支持林的創作,並鼓勵他打造自己的現代主義。這些歐洲前衛藝術家的影響在展覽中最早的兩幅畫作中顯而易見,《Le Désastre》(1938年)著重刻畫解構空間中的三個人物,還有一幅研究椅子上的女人的作品《Sans titre》(約1942年),它們忠於立體主義原則,與其餘30多幅作品截然不同。林隨後在1940年代初回到哈瓦那,催化了他的風格上的演變。他將非裔古巴人的宗教桑特里亞(Santería)的精神實踐融入到他所描述的「心理–生理學的原始主義(pyscho-physiological primitivism)」的視覺詞彙中,並對幾個世紀以來古巴被殖民主義剝削後普遍存在的旅遊退化現象感到不滿,開始創作憤怒的、夢魘般的繪畫。 他寫道,「我回來時看到的東西,就像某種地獄。對我來說,販賣一個民族的尊嚴就是這樣:地獄。」用他的話說,從那時起,每一幅畫都是對這種墮落的「驅魔儀式」。
《The Casting of the Spell》(1947年)體現了這種象徵式的驅魔儀式。這幅不祥的畫作採用了渾濁的黃灰色調,呈現了林許多作品中出現過的馬頭女郎。在桑特里亞的儀式中,參與者在被神靈附身或「騎乘」時被稱為「馬」。與Paul Gauguin描繪的原始、被馴服的女人相反,「馬頭女郎」引導著桑特里亞神靈附身時發生的、根本的精神轉變。林並沒有將女性形態與可識別的身體聯繫在一起,而是將所有先於既有的女性特徵原型串起來,創造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人類手臂和乳房、球形附屬物、月牙形和鳥類頭部的複合體。
林回到巴黎後於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創作的作品中,人物變得越來越細小,幾乎成了樹枝狀。例如,《Personnage》(1970年)刻畫了兩個貧血的人物,以深灰色背景襯托出鮮明的輪廓,遊走在形象和抽象的邊界。這件作品介於Louise Bourgeois的圖騰雕塑(有著類似標題《Personnages》)、20世紀初建構主義體現的清晰的形式、以及Joan Miró的繪畫的無序性之間。左邊的人物以分叉的軀幹站立,和展覽中幾乎所有其他畫作一樣,它身上標記著鋸齒狀的點,看久了令人感到痛苦。
憑藉反復出現的刀削般的形式、角度和牙齒,林的畫作充滿了飽受折磨和無情的味道。林將自己的作品概念化為「一種去殖化行為,不是身體意義上的,而是精神意義上的」。他的作品中的心理效應截斷了歐洲現代主義和古巴本土傳統的不可比性,造就了尖銳的秘密圖像,看起來和以前的任何創作都不一樣。鑑於林的作品能夠在歐洲、北美和拉美前衛藝術的最高圈層之間游刃有餘,我們很容易將其簡化為簡單的「多元文化」。但實際上,他與歐洲前衛藝術體制有著異常複雜、不安的關係,甚至與他的密友Picasso也是如此,Picasso和他的原始主義概念在晚年與林漸行漸遠。從這個展覽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這種文化和美學的「混合性」在林飛龍的藝術生涯中不僅僅是不同「影響」的結合,更是一場漫長的噩夢或持久的騷動,是長期致力於自我解放的美學的努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