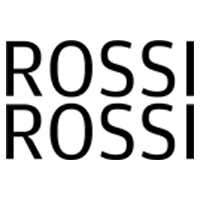安特衛普:多元化視野
By Nav Haq

Installation view of JUMANA MANNA’s "Thirty Plumbers in the Belly," at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ntwerp (M HKA), 2021. Courtesy M HKA.
這裡既有組織上的「螺母和螺栓」問題,也有藝術上的問題。讓我們從2021年運作上的實際問題開始。與我們的荷蘭和德國鄰居不同,比利時的博物館全年保持開放,包括安特衛普的M HKA,這裡的當代藝術博物館。儘管如此,像其他人一樣,我們不得不每天處理疫情的問題,儘管前一年進行了大量的情景規劃、來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來再次啟動這些項目。這感覺很好,也很有象徵意義,參觀者信任博物館,而參觀博物館本身就是一種社交距離措施。與亞洲的同行交流時,我們詢問了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是如何設計新標誌的,以及森美術館在重新開放前採取了哪些措施。長時間下來,我們本已通過藝術對話、歷史研究、展覽和收購來發展歐亞軌跡,而這些跨大陸的交流更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支持這些歐亞軌跡,儘管人們對全球化的生態和社會經濟影響感到擔憂,但文化領域的多極對話仍像以往一樣重要。
今年年初的展覽是「Monoculture – A Recent History」(9/25/20-4/25),這是一個特別複雜的基於研究的展覽,對上個世紀的文化同質性進行了分析。通過對社會、農業、語言、甚至解放範式的案例研究,展覽描繪了單一文化是存在於各種世界觀中的東西,通常不利於發展真正多元化的文化、且具有禁錮的效果。當地的陰謀詭計、地緣政治、暴力、健康危機和其他各種黑惡勢力日益成為不可避免的背景,也成為了我們展覽內容的背景。我們至少在George Floyd被殺害前一年就決定在「Monoculture」中展出Andy Warhol的印刷作品Birmingham Race Riot(1964年);或者Ibrahim Mahama的雕塑《On Monumental Silences》(2018年),當我們考慮到它們的暴力圖像,我們現在會如何看待?如果得到有意義的處理,這些問題也應增強文化機構工作和社會辯論之間的關聯性。
夏天,我們展示了Shilpa Gupta的首場回顧展「Today Will End」(5/21-9/21),回顧了她20多年的經典作品。其中包括她的代表作《Singing Cloud》(2008–09年),這一件抽象作品,對無意識和恐懼的心理進行了催眠般的探索。在展覽準備期間,印度被封鎖了。與其他關鍵作品一起,如《Today will end》(2012年)和《Threat》(2008-09年),我們看到Gupta的作品有一種「可翻譯性」,與地方和時間相呼應。同時,「Thirty Plumbers in the Belly」(5/2-8/29)是與Jumana Manna合作的一項、充滿野心的新委託作,她有一種深刻的能力,能夠在系統的崩潰中感知希望和活力,同時考慮那些注定失敗的、即興建起的基礎設施中的美學。在展覽進行期間發生的Sheikh Jarrah驅逐危機和加沙爆炸事件中,這個展覽感覺特別強烈。

ALIGHIERO BOETTI, Mappa (Mettere al mondo il mondo), 1971-73, hand embroidery on linen, 163 × 217cm. Photo by M3Studio. Courtesy MAXXI, Rome.
展覽「Eurasia — A Landscape of Mutability」(10/8-1/23/22)為我們的觀眾提供了20多年來對進步的歐亞主義可能是什麼的思考的整合。我們在這裡把歐亞大陸理解為擁有文化的多元性,在不同程度上協商傳統和快速的現代化,並且在考慮到新出現的權力平衡時,也理解為未來性。認識到這些因素是如何為藝術家創造實踐條件的,「Eurasia」是一個跨歷史的展覽,通過大約50位藝術家的作品來捕捉這個超級大陸的藝術折衷主義。在定義我們的文化和概念空間時,「歐洲」和「亞洲」的定義越來越被放逐,而傾向於已經開始定義21世紀的特定多元化。
在期待與歐亞大陸廣闊空間所承載的多元文化進行更多接觸的同時,我們自然會在這個世界觀中看到我們的位置。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港口,安特衛普是166個不同民族的正式家園。我自己的社區就在安特衛普中央車站以北,現在是一個葡萄牙人、西藏人、阿富汗人和弗拉芒工人階級的社區。歐亞大陸已經在這裡了;現在也是時候在我們自己的地方參與了。

Installation view of PEJVAK’s Invocation (An Incitement to Ruin), 2021, bricks, mortar, concrete, and pigeon spikes, 450 × 450 × 180 cm, at "If Need Be," Z33, Hasselt, 2021. Photo by Rouzbeh Akhbari. Courtesy the artists and Z33.
在2021年有限的旅行中,我更深入地探索了安特衛普、佛蘭德斯和該地區。這裡有新生代和接近中生代的藝術家們(Mathieu Verhaeghe, Hana Miletić),也有自我組織的活動(Table Dance, Out of Sight, Jubilee)的繁榮景象;有尼日利亞出生的藝術家Otobong Nkanga和法國藝術家Laure Prouvost等人的積極影響,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覽,其中的亮點是藝術家二人組Pejvak(Felix Kalmenson和Rouzbeh Akhbari)在哈瑟爾特的Z33舉辦的展覽「If Need Be」(6/12-8/22)。他們在歐洲的首場個展,探索水的稀缺性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如費爾幹納山谷。與此同時,許多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在過去的兩年裡遇到了困難,機構和政府充分了解了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嚴峻現實,在建立藝術家收費和付款的國家模式方面終於取得了真正的進展。
在一次對荷蘭機構的深入訪問中,我面對的是與來自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領域的話語相媲美的非殖民化詞彙。它給人的感覺是代表性和高度單一的文化,是一種新的文化正統的不斷排練,缺乏基本的批判性。與其說它是一場運動,不如說它更像是一種群體思維,因此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那些可能不願意順應它的人的位置是什麼?雖然我們正在關注類似的平等、多元和共存的問題,但我覺得在佛蘭德斯,話語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展開,無論是文化上還是哲學上,都有比利時思想家Chantal Mouffe啟發的「爭勝式」思想。這需要激進的想像力,但也許我們需要在身份自由主義存在的同時,找到新的社會和文化自由主義的替代形式——後身份的社會文化自由主義,解決人類主體性的更廣泛的語域。正確的條件就在這裡;一種更加即興的文化精神,而不是群體的一致性,而且沒有身份政治等歷史運動的包袱。它已經感覺到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當務之急是藝術智慧和機構實踐能夠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請關注這個空間。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