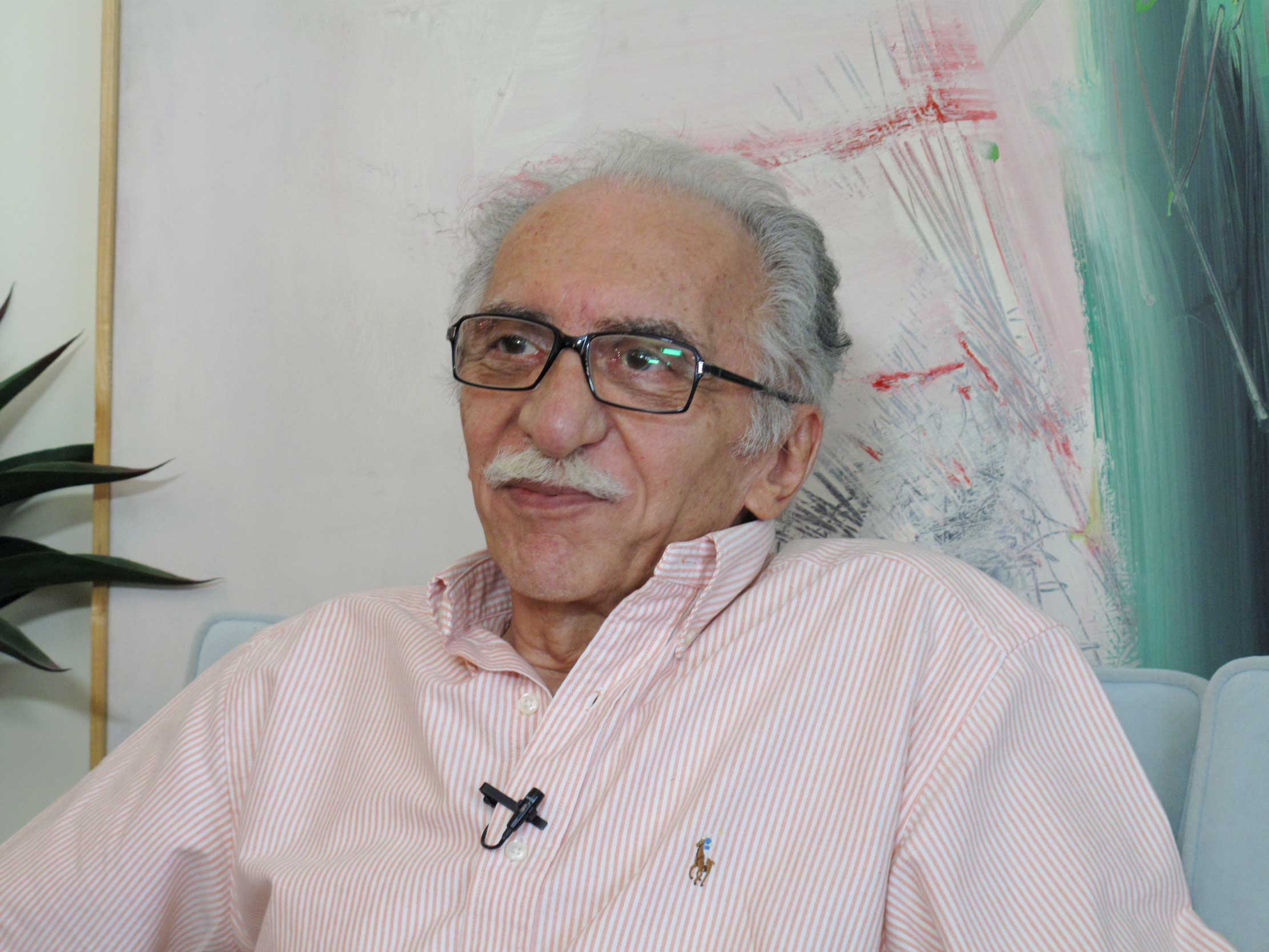中文
一對一:梁志和談Christian Boltanski


20世紀80年代末,我在香港一所藝術學院學習。當時,香港這個前殖民地的未來已被一個日期所決定,但這個日期對我來說卻是遙遠的——十年對於一個少年來說非常漫長。我那時還很天真,藝術、社會、身份和主權的概念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我的一位老師曾經說過,香港的藝術趨勢比西方的主流藝術晚了十年。許多活躍的藝術家都在做新表現主義的繪畫,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多數同學也都專注於此。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並不擅長畫畫。我開始嘗試不在學校教授範圍內的攝影。可以說,我有點太以自我為中心,傾向沈溺過去、懷念年少時無憂無慮的時光。讀書的第二年,我找到一份在美國的暑期工,計畫計劃工作結束後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背包旅行。那是1988年,我旅行的最後一站在洛杉磯。在當時被稱為MOCA’s Temporary Contemporary,我參觀了一場美麗的展覽,在昏暗的燈光下有許多小尺寸帶有畫框的黑白兒童肖像、復古服飾、以及成堆的金屬盒子,還有一個壯觀但精緻的的皮影戲裝置,我對它了解不多。當我走近這些作品時,有一種緊張感,在這些裝置前的複雜體驗很難描述。不過,我的確被感動了。照片中展示的兒童和被畫框裝裱起來的衣服似乎有某種指向性,一方面指向某種文化背景下的獨特敘事,但另一方面也有全球共通性。
我對這個展覽的印象非常深刻,拍了很多照片。我不認識這位藝術家,也不知道如何拼讀他的姓氏。回到香港後,我只記得他的名字是Christian。那是一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我找不到任何關於這位藝術家的書。幾個月後,我在《Art in America》上看到了關於這個展覽的專題。是的,他就是Boltanski,這位為自己和他人被偷走的童年而哀悼的藝術家。作為一個20歲的藝術學生,我第一次深刻了解到死亡這一概念。死亡,並非作為一個人生命的結束,而是作為歷史的終止,因為歷史可以被再創造,就像Boltanski在他的紀念碑式的雕塑中所做的那樣。在他的作品中,個人記憶得以活現,他鼓勵我們去克服或反思令我們覺得棘手的過去。
畢業後,我不確定是否要繼續從事藝術,但盡全力推遲對自己的未來下任何定論,我還想繼續旅行和學習。我和同伴去意大利露營,我們的第一晚在翁布里亞湖的馬焦雷島上的一個小公墓旁度過。在那裡露營是違法的,但周圍沒有人。我們在太陽下山時才搭起帳篷以免引起注意。那天晚上,我經過骨灰堂的大門,走到自來水龍頭前。我看到一牆的壁龕,每一個都放置著微型的肖像和蠟燭瓶。這不禁讓我想起Boltanski用小燈照耀著無名畫像的裝置作品,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他所指向的東西。在那裡,我沒有感覺到任何恐懼或悲傷,只有平靜和安寧。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可以被簡化為純潔。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卻沉浸在一種沉靜思考的狀態中,就像在面對能劇表演中的無聲時刻一樣。
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Boltanski的藝術語言非常容易理解,他頻繁出現在各個藝術媒體的報導中。我很快發現我的香港朋友都成為了他的粉絲。他的知名度也隨著藝術機構對符號學的廣泛研究而上升。 1996年,Para Site的首場展覽「Relic/Image」 也反映了這一趨勢。這一展覽參考了David Clarke 於1992年寫作的文章「The Icon and the Index:Modes of Invoking the Body’s Presence」中的觀點,即攝影和懷舊的老物件作為媒介擁有超越宏觀敘事的功能。我意識到,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計劃和記憶,但Boltanski提出的遺物(relics)的概念,即藝術作品作為藝術家的遺物而博物館作為墓地,仍然具有跨文化和跨時代的共通性。
在Boltanski於2021年去世以前, 他的存在感在近幾年已逐漸消退。我從未有機會見到他本人,但偶爾在展覽中看到他的作品時,我仍會想起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時的經歷。他的作品允許矛盾的存在:既是對記憶和過去、對某個個體和所有人的慶祝,也是哀悼。雖然我沒有參觀過他於日本手島展出的收集了世界各地人們心跳的裝置作品《Les Archives du Coeur》(2010年),但我覺得那種面對他的作品的感覺,我已經在馬焦雷島體驗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