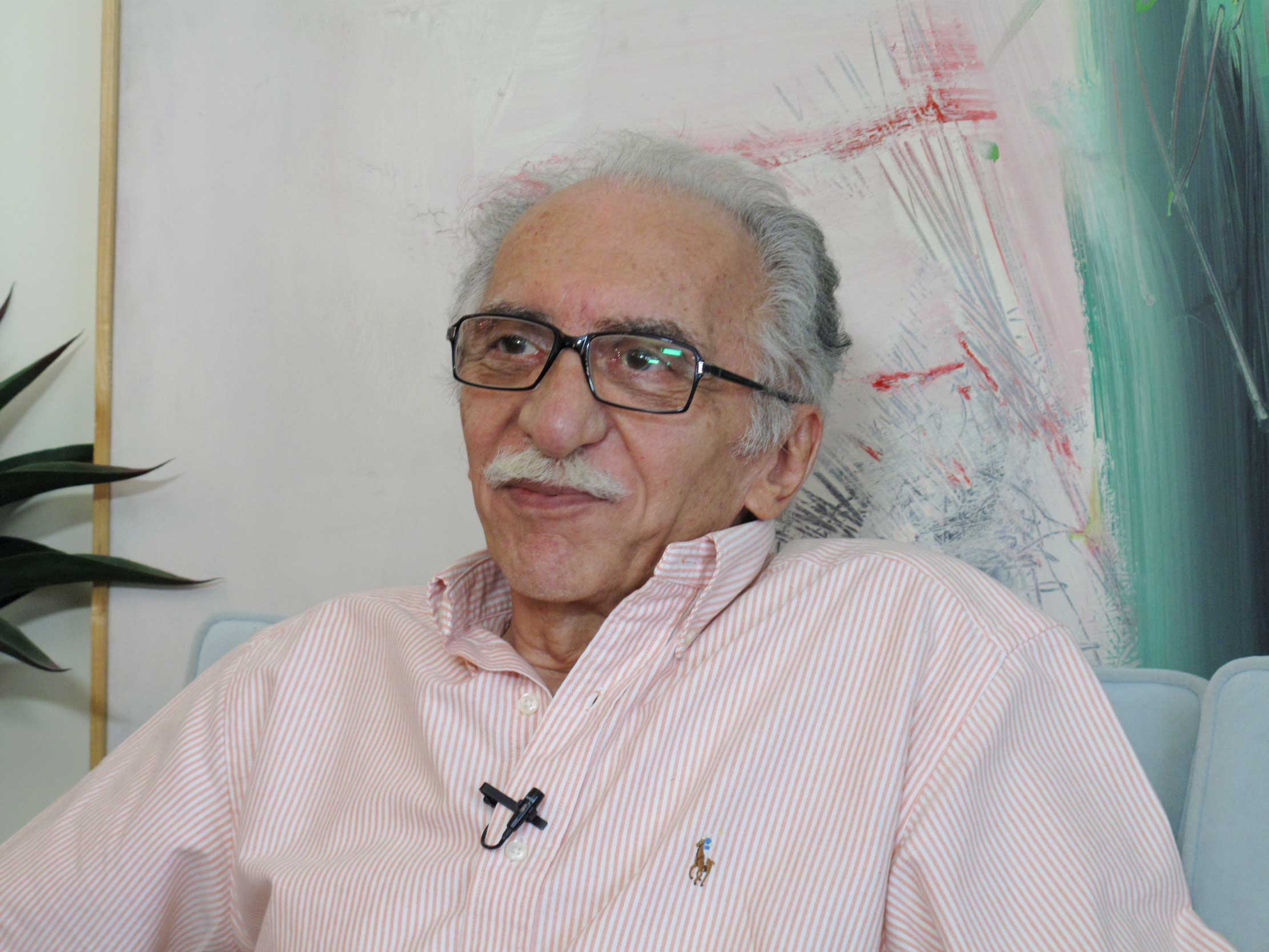中文
慕尼黑:中谷芙二子


中谷芙二子在日本以外的首場回顧展「Nebel Leben」將Haus der Kunst龐大的東翼展廳改造成一個帶有半懸浮地板的霧狀池塘空間,每隔半小時釋放出霧氣。厚重而異常混濁的霧盤旋、移動、將觀眾包裹成一個蓬鬆的群體,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個繭。這難以捉摸的體驗帶來一種安靜的眩暈感。當霧散去,我們似乎從夢中醒來。環顧四周,天窗下的環境突然顯得清爽,即使霧的消散令我們懷疑我們是否高估了能見度。
50餘件多變的作品當中重點展出的中心作《Munich Fog (Wave) #10865/I》在壯觀的灌溉系統嘶嘶作響。觀眾走過的木製平台下有一條幾英寸深、平靜的運河。管道上的噴嘴閃爍著凝結的水滴,瘦小的軟管蜿蜒進水中。在俯瞰英式花園的露台上,第二件新作品《Munich Fog (Fogfall) #10865/II》的煙霧從屋頂簷口的管道中飄出。它嘶啞的水氣變得模糊,展露了納粹時代建築令人不安的紀念意義(這也是博物館現在進行中的翻新計劃中的一個焦點難題)。人的皮膚和衣服也變得潮濕,博物館員工需要穿著雨披在室外工作。
藝術、生態和工程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中谷作品中的標誌,她堅持機械也是可見可聞的。與其說她的霧氣雕塑是超凡脫俗的,不如說是一種回歸大地的沉浸,她的作品強調我們忽略的自然景觀在表演時如何重新吸引人類的注意力。這位出生於北海道的藝術家今年5月剛滿89歲,在全球展出過90多件霧雕作品。1966年,Robert Rauschenberg和貝爾實驗室工程師Billy Klüver於1970年大阪萬國博覽會發起的傳奇跨學科團體,藝術與科技實驗團體(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E.A.T.),而中谷是最早的參與者之一,並首次在萬博會上安裝了第一件這樣的作品。她的物理學家父親,即人造雪的發明者,中谷宇吉郎也影響了她早期的創作(也是展覽中其中一個展廳的主題)。藝術家在1989年獲得了水霧裝置的專利,並不斷改善硬件,務求令水滴越來越接近真實的霧的濃度。在Haus der Kunst,高壓的水被壓緊不鏽鋼噴嘴中,被分成17微米的細小尺寸。
「Nebel Leben」展出了中谷共28件畫作,預示了藝術家後來對大氣的偏執。繪於透寫紙上的設計方案精緻地說明了她將設想具體化的技巧。在描繪水箱、過濾器、泵和閥門的同時,這些畫作將霧狀物遮擋或擦拭成攪動的岩漿或蓬鬆的絨毛。在1958至1964年創作的10幅油畫中,像《Sun》(1960年)這樣沾有污漬的、紅色的抽象畫喚起原始的風景;在其他畫布中,複雜的結構令人聯想起葉子、細胞和鰓。《Body Cosmos》(1964年)和《Cloud Series》(1964年),這兩幅格外詭異的、精湛的畫作中能看出原子彈爆炸的影響,描繪了懸浮在陰暗的綠色深淵中的肉體和哭泣的雲朵,藝術家自己稱這些畫為 「分解」,並談及她對 「出生和死亡的過程整個週期」的迷戀。
中谷在形式優雅的錄像作品中也探索變形:《Coordination: Left Hand / Right Hand》(1979年)中刺耳的削鉛筆聲;《Columbus Story》(1973年)中將一個完整的雞蛋豎起來的過程,以及《Sōji-ji》(1979年,令人遺憾的是,這是展覽中唯一強調中谷豐富日本背景的作品)中慢步行走和念誦的禪宗僧侶。展覽入口處的牆面錄像《Ride the Wind and Draw a Line》(1973年)中,一隻蜘蛛在勤奮織網。這一明確的策展角度確立了中谷作為日本錄像藝術的推動者、作為一位藝術全球網絡化的關鍵人物的地位。
「霧的狀態是非常民主的。」中谷在2007年的採訪中反思道。「它不斷地移動,當兩個水滴相撞時,它們各自遠離一點,為彼此騰出空間。它令世界變得更大一些,讓每個人都能生活在其中。」她的作品不僅不斷擴張著藝術世界的範圍,而且融合、幻化成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