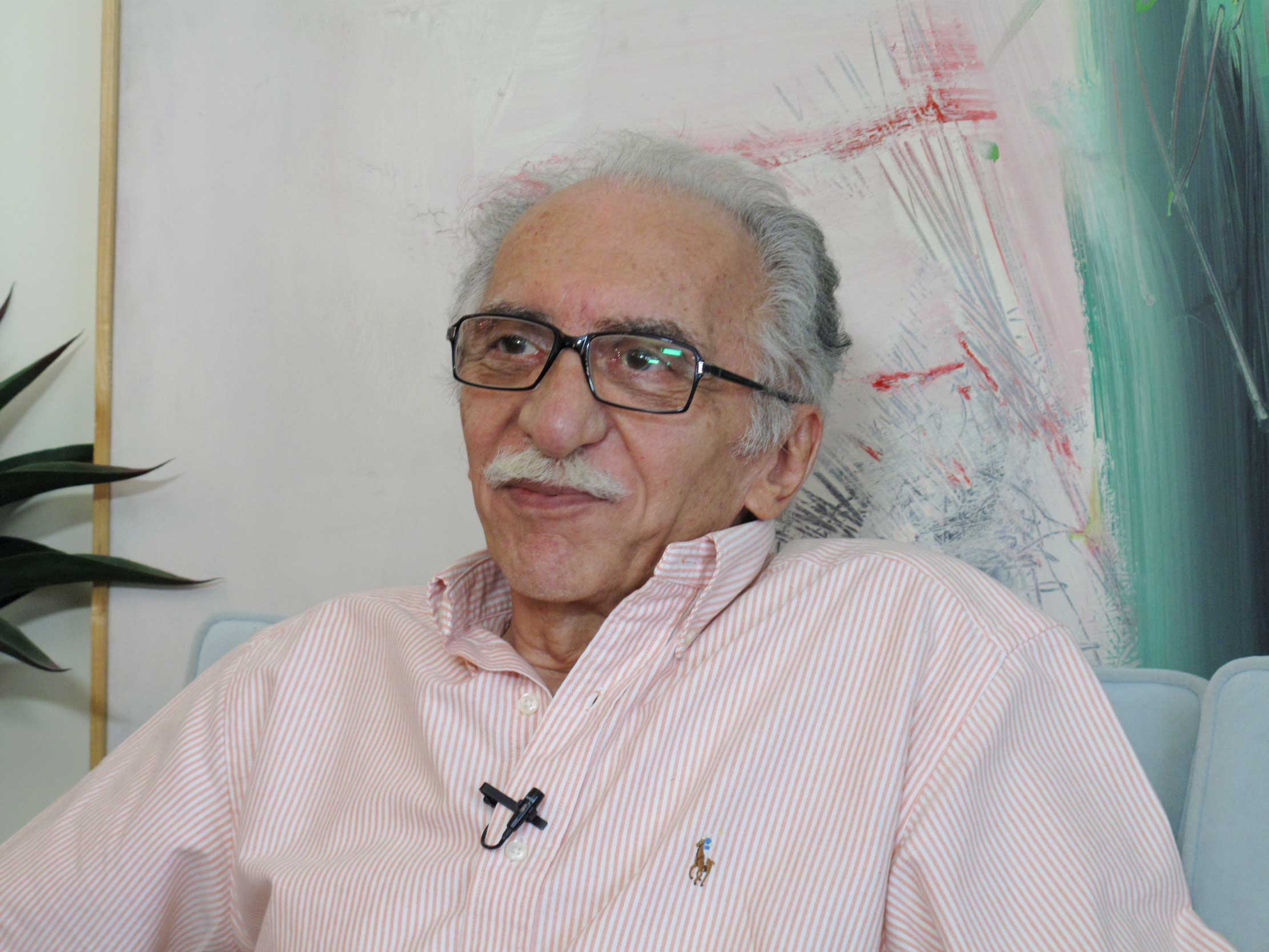中文
柏林:來勢洶湧


2022年1月,柏林一群藝術家發起了一場抵制運動,撼動了當地藝術界。其中聲量最大的藝術家是Candice Breitz,他發起了一場草根運動,反對在前Tempelhof機場新建Kunsthalle Berlin展館。Tempelhof機場被改建為該市最大的歷史文化空間之一,每年舉辦藝術博覽會和音樂節。「Kunsthalle」即「藝術館」,以城市冠名的藝術館通常是非營利藝術空間。這一項目之所以受到抨擊,是因為人們發現,Kunsthalle Berlin的主管機構Foundation for Art and Culture,作為一家私人基金會,卻在背地裡從柏林市政府獲得場地和資金,還與俄羅斯總統維持著友好關係。此後,Kunsthalle Berlin項目暫停,明年將公開徵集意見,決定機場的未來。這場公開爭議一直持續到年中,似乎預示了德國持續全年的藝術和政治之間的糾葛,並展現了柏林遲緩的政府機構之下的藝術先鋒文化。
在這一年裡,德國首都在疫症兩年後急需恢復正常線下生活,但隨著戰火在1200公里之外的基輔燃起,柏林又在經濟與生態戒備之間搖擺不定。1990年代柏林藝術界的領軍人物和美國主要藝術機構的前負責人Klaus Biesenbach,最近擔任Neue Nationalgalerie的新館長,率先帶領推動文化團結。當許多人正在努力應對突然湧入的烏克蘭難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造成的致命短缺時,這家博物館在東歐衝突升級後的幾天,於三月初組織了一場臨時的長達48小時的為烏克蘭守夜活動。儘管這場活動最初被認為是一個宣傳噱頭,但它最終成為2022年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數以千計的人排隊捐款,Anne Imhof和Olafur Eliasson等藝術家開展了公共論壇,在早期的階段對此後長達一年的戰爭中提供了希望。

在此後這一年,很少有像這樣及時又有意義的藝術活動。例如,備受期待的第12屆柏林雙年展,名為「Still Present!」(6月11日至9月18日),由藝術家Kader Attia策劃,卻沒有探索出新鮮的藝術潮流,而是總結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殖民歷史。在這個城市的其他地方也有令人信服的國際展覽。Dahlem地區的Brücke Museum在新一年裡舉辦了罕見而充滿吸引力的展覽「Whose Expression? The Brücke Artists and Colonialism」(2021年12月18日至3月20日)。該展覽由一隊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元化團隊策劃,由策展人、編輯部和外部委員會組成。展覽認真審視了博物館內的表現主義藝術藏品中的南太平洋殖民主義幽靈。Hamburger Bahnhof博物館的 「Nation, Narration, Narcosis: Collecting Entanglements and Embodied Histories 」展覽(2021年11月28日至7月3日),是該博物館與雅加達、新加坡和清邁之間機構合作長達數年的成果,展示了多位東南亞年輕藝術家的引人注目而詳盡的藝術作品,並舉行了探討國家建構的線上對談和講座。 Savvy Contemporary的「Garden of Ten Seasons」(6月10日至7月10日)和KINDL的群展「Landscapes of Belonging」(3月6日至7月3日)都呼應了這一年的重要藝術活動——尼泊爾的加德滿都三年展和威尼斯雙年展的北歐館,它們將不同的宇宙觀和被忽視的土著人的抗爭從世界上不同地區引介到柏林。


也許是為了矯正疫症中盛行的反亞裔情緒,較小型的美術館和空間展示了一些年輕的中國藝術家的個展,例如Peres Projects舉辦的李爽的個展(4月29日至5月27日);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s舉辦的何翔宇展覽(4月29日至5月28日);Wannsee Contemporary舉辦的aaajiao(徐文恺)展覽(5月1日至7月16日);以及daadgalerie舉辦的郝敬班展覽(10月21日至12月18日)。
到了秋季,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和令人擔憂的燃氣價格,令人們熱烈討論下一個 「Kulturmilliarde」,這是繼貨幣援助之後德國第二個 「文化十億」計劃,以幫助藝術界勇敢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與此同時,一份媒體報告顯示,第一輪資金分配無序,導致大量資金流入商業藝術領域。儘管這一消息並不令人意外,但還是有些令人挫敗。德國第十五屆卡塞爾文獻展的藝術指導ruangrupa團體顛覆性地採取了印尼的公共米倉「lumbung」,作為策展的核心概念,令這次五年展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4200萬歐元(5100萬美元)的預算,相比之下,德國的文化資金卻陷入了其自身複雜的官僚體系的困境。
雖然市政當局目前正在跨過自己製造的障礙,但柏林藝術界的凝聚力卻像以往一樣強大,充滿活力。在即將來臨的嚴冬和無法預見的社會政治動蕩之下,這裡的藝術集體希望創造連結,向新的文化主導力量過渡。 2023年1月,Savvy的創始人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將接管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希望他能克服柏林遲緩的官僚主義機器,並迫切地對柏林的創意行業作出改變。